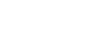“天朝上国,皇恩浩荡”“万国来朝,大国威仪”“八方来贺,四海宾服”……这些流行于史书、碑铭和外交辞令中的一句句响亮口号,折射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外关系的一种文明姿态。
自汉唐以来,中原皇朝一直以“天朝上国”自居,其对外关系的核心架构,是那套被后人称为“朝贡体系”的制度安排。
在这一体系中,藩属、外国王朝需按期或不定期遣使朝贡,以示对天子皇权的尊重;
而中原皇帝则慷慨“回赐”,不仅物资丰厚,甚至远超所贡数十上百倍,引得周边“万国来朝”。
“封赏”为何如此之丰?
若没那丰厚赏赐,边疆小国恐怕不会那么积极地远道而来。
但这,也许只是中原“穷大方”的自娱自乐。
一、从周汉礼制探索
朝贡制度源于西周,当时的朝贡,更多是一种盟主式的诸侯进献,象征政治从属,基本无殊利可图。物尚质朴,形式重于功利。
到了汉武帝打通西域路线,尤其自张骞通大月氏后,“四夷来朝”成了王权对外的一种展现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,大宛、身毒、乌弋山离等纷纷遣使,“献其奇物”。这些贡品名称虽奇,实则价值有限,却能换来中原“赏赐锦绣、金帛”的数倍回赠。
元帝时还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乌弋国贡铁马一匹,高宗赏金五百两。”一匹金属马,可得如此赏赐,可见汉帝国的“沽名之重”。
然而汉朝不同于后世,国力初强,亦欲借“广交远人”加持其制度自信。
所谓“朝贡”,在很多边地政权心中,其实是一次传统意义的“进货与赚钱”机会。
但此时的汉代并未全面推行“厚往薄来”,物资回赐多因外交需求而择国厚待,尚未形成制度性的一体安排。
二、唐宋:当“厚赏”成为财政预算
进入唐代,“厚赏”变成了一种制度性安排,几成标配。
唐太宗治下,《旧唐书·东夷传》列明:“倭国来朝,所贡薄品,天子大喜,赐其王金器锦绮百余。”以小献而获巨利,未必因为物之稀贵,而是“朝之而顺”,是对文明秩序的认可,朝廷自然要“广施仁政”。
最为人熟知者,是新罗、渤海等朝贡路线之繁密。
《册府元龟》卷五百三十三载:“渤海每岁来使。贡尚书令以下,赏金、器、物不可胜计。”
《唐会要》提及:“诸蕃所贡,率皆土产,然所赐绢帛金银十倍于贡者,不可胜数。”
此时的赏赐计划已有专门财政编制支持,乃国家正常支出。
唐朝还规定:“朝贡必有宴,酒食器皿皆由鸿胪寺供给。”甚者,国子监设朝贡类子弟学额,以收“文化整合效应”。
“厚往”,是皇帝的面子,是文化自信的体现,也是帝国边疆战略的组成部分。
唐玄宗时期,回赐物资动辄千余匹绢帛,形成制度化运作。朝贡成了外围政权的“高回报外交”,激励其不断来贡。
但“厚赏”是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,唐代后期,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库大空,回赐已力不从心,甚至记有“夷使候赐三载而无果”的窘态。
礼仪背后,是经济支撑,而礼仪无法遮掩国力衰退时的尴尬。
宋重“厚赐以维藩服”,虽商业发达,国家富庶,但却过于重文抑武,外交软弱,让其中原“圣天子”形象在契丹、西夏、金面前被严重削弱,这种情况下,更要花钱买“平安”。
三、明代:郑和七下西洋=大型“撒币”现场?
若论朝贡制度的鼎盛辉煌,莫过于明永乐年间。朱棣因得位不正,为强化开国合法性,同时寻找建文帝,派遣郑和“宣化四海”。郑和七下西洋,不仅传播天朝声威,更几乎是在展开一次又一次的“外交馈赠竞赛”。
据《明实录》和《星槎胜览》记录,暹罗国献象三头,便得黄金五百两、彩绸千匹,香药换来“千两回赐”。阿拉伯地区(彼时称“天方”、“忽鲁谟斯”)诸国朝贡者,常以珠宝、马匹为献,而明廷照例回赐十倍左右。原材料产地的贡品,通过“官方批发差价”,成为明帝国夸示的工具。

这也直接造就了琉球国历代国王一直极重视“扈从明使、朝见贡使”的外交事务,《琉球国志略》甚至记有“贡若不停,则国足有用”之语。对琉球等诸小国而言,这等于“国家公务出差带货赚钱”的模式,甚至成为国家财政供血系统。
然而,换个视角,我们也须问:是谁在买单?
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载:“朝贡使至,内府拨银供应,不计耗。”
钱从哪来?从财政中来,而财政来自赋役与矿税,终归落到百姓头上。
“一赠天下,十取于农”,诚非虚言。
四、清代:乾隆的“万国来朝”只是一场Cosplay
《大清会典》详细规定:“诸藩贡品,不必贵重,所赏以国态为允。”。
清代乾隆帝称“十全老人”,好大喜功,尤喜“万国来朝”之盛景。乾隆五十年(1785),大英使团马戛尔尼来华,虽未开放通商,却所求回程之利,皆大为优渥。《清高宗实录》确载:“予赐其贡臣以缎千匹、古器百物。”其使团回欧洲后对外宣称“此次远来获利数年”。
乾隆知其如是,却亦欣然为之。因这一套机制早非实际外交,仅为中原自信与道统的“复刻展演”。“我朝天朝,夷人虽异,惯听命耳。”视野之封闭,实乃制度之自缚。
更严重的是回赐规模增长之机制未缩,而实际政治边远化、外贸通道流入却减,让皇恩变成“虚支”。

清末国力每况,咸丰时赈灾告急,朝贡赏赐仍不止。一边“民不聊生”,一边“礼遇朝贡”,诚如学者赵尔巽所讽:“宫中之偿,国中之乏”。
五、面子与里子
从上千年的实践看,“厚往薄来”确实造就了中国与周边政权之间独特的经济互赖模式。
对中原而言,它是建立威信、吸引顺服、输出秩序的手段。
但是,这种制度其实并不经济理性,由国家层面补贴“虚荣工程”。一度引致财政困难、商贸短缺,普通百姓或被加税负担;
对周边政权而言,却是对冲政治不安乃至积累财富的绝佳捷径。于是出现了“假贡真商”“一贡多使”等现象。史有记曰:“安南每贡一物,而来使三番,朝中不察也。”
可以说,这种制度的运转,关乎皇帝的脸面,也关乎整个体制的文化需求。大国的“面子经济”,有时并非大方慷慨,而是虚荣的制度维系。
中原王朝借助“厚往薄来”构筑了虚实结合的国际秩序。但这光鲜外表之下,实藏着资源耗费、财政透支、外交“反市场化”分配的深层隐患……
责任编辑: